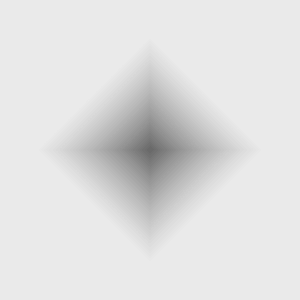熱門話題
#
Bonk 生態迷因幣展現強韌勢頭
#
有消息稱 Pump.fun 計劃 40 億估值發幣,引發市場猜測
#
Solana 新代幣發射平臺 Boop.Fun 風頭正勁
一個帝國失去的最後一樣東西就是它的傲慢。
即使在自我羞辱的時候,它也帶著醉漢的狂妄。
在任何大國的崩潰中,有一個特定的悲喜劇階段,當它不再構成威脅而開始成為一場表演。傲慢是唯一不需要預算、功能性供應鏈或忠誠公民的東西;它是衰退精英的無限資源。當一個帝國開始腐爛時,它不會安靜地退出舞台,而是絆倒在舞台燈光前,摔壞布景,同時要求觀眾為它的「對重力的勇敢重新詮釋」鼓掌。
這是一種心態,你絕對確信自己正在贏得戰鬥,即使你目前正被一個你拒絕承認的現實鎖住。
歷史上,這表現為拒絕適應自己失敗的氣候,就像殖民官員堅持在悶熱的熱帶氣候中穿著全毛料的正式制服和粉飾的假髮。即使當地居民開始離開,總督們仍然專注於杜松子酒是否冷卻到精確的帝國標準。
在現代背景下,我們看到這種技術官僚對微觀規範的痴迷,這些規範支配著生活中最小的細節,而宏觀結構卻在崩潰。當一個文明失去建設大型基礎設施、解決能源危機或贏得決定性衝突的能力時,它轉向唯一仍能大量生產的東西:規則。這是電子表格的傲慢,領導階層可能無法為公民的家提供暖氣,但絕對會確保每個家用電器都有一份二十頁的安全手冊,翻譯成數十種語言。
這一衰退中最危險的部分是最後一擊,試圖證明這個實體「仍然有能力」,通常被稱為醉漢的揮拳。這些是絕望的嘗試,想要看起來像一個全球參與者,最終卻意識到銀行賬戶已經空了,鄰居已經報警。這是地緣政治上類似於一個人在派對上試圖做後空翻以取悅前伴侶,卻最終摔成了骨科石膏;真正的羞辱不僅僅是摔倒,而是他真心相信自己會成功著陸。
這種傲慢作為一種生存機制,因為承認真相會使整個社會幻覺瞬間消失。相反,衰退的帝國加倍努力,建造一個閃亮的新總部,而舊的總部正在被收回,或者為一種越來越被用作壁紙的貨幣啟動重新品牌運動。它向世界其他地方講授其「優越的價值觀」,而它自己的首都城市卻開始像後末日電影的場景。
然而,最終的諷刺在於,這些衰退的力量仍然堅持從一個崩潰的講壇上向全球講授。即使這些衰退的力量積極拆除自己遺產的基礎——將自己的歷史視為一個犯罪現場而非基礎——他們仍然對自己作為世界道德巔峰的地位保持著奇怪而堅定的自豪感。他們會大聲譴責那些建立他們文明的祖先和機構,但在同一口氣中,卻要求普遍遵守他們最新的、短暫的文化框架。

熱門
排行
收藏